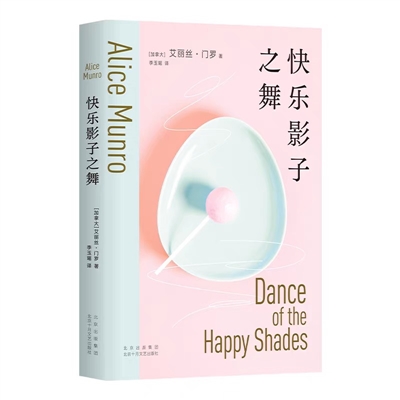文/陈幼芬
读完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总觉得她在教我一件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颗多棱的钻石,有的棱面被阳光照着,比如勇敢与自信,像挂在胸前的勋章,亮得人一眼就能看见。可有些棱面,总被我们悄悄转到阴影里,比如敏感与脆弱,好像它是一种见不得光的病。但门罗偏不,她捧着自己那颗钻石,把敏感的那一面充分地折射出光来,结果整颗钻石亮得更为惊人,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十三位获奖女作家。
《快乐影子之舞》集结了15个短篇。门罗的文字仿佛洞悉一切,她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创作了15位小镇女性的生命故事。敏锐的双眸,速写一般将捕捉到的人性最幽微的部分一一呈现。她也像一位生活的观察者,将平凡的人们惯常忽略的细节琐事,赋予了深刻意义。门罗的叙事,总是带着模糊的滤镜,既清晰又朦胧,主人公的痛,是个体的,也是大众的。她关注事件背后复杂的人性与偶然,没有简单的对错判定,没有精准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种模糊性,更让人禁不住在字里行间产生属于自己的思考。
《死亡时刻》里的母亲利昂娜,就是块被痛苦磨出尖棱的石头。那天的情景有些混乱:利昂娜要出门办事,她的四个孩子都在屋里玩耍。但一系列偶然的因素——成人的短暂疏忽、孩子的天真好动、环境中潜在的危险,悄悄叠加出一个悲剧:一岁半的本尼丧生于帕特里夏拿来拖地的滚烫热水里。就在离开屋子的四十五分钟里,她最小的儿子刹那间遭难,利昂娜哭得歇斯底里,不停对九岁的帕特里夏大声嚷叫——“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她把火全撒在了她最大的女儿身上。门罗并没写“她很痛苦”,但“她盯着女儿时责怪的眼神,向邻居诉说时哀怨的神情,时不时地低声哭泣”,门罗写的是“她痛不欲生的心里,从此结下了一道解不开的疤”!帕特里夏呢,面对“无心之失酿成的悲剧”,她没有哭,一直沉默着,偶尔“疯”一下情绪,她的心里,因“照看弟弟的隐性责任”与“我没有尽到责任的自责”,也落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疤。唉,那些向外扎的刺,正是自己心里没处安放的疼啊!
《男孩和女孩》是另一个动人故事。父亲是狐农,狐狸维持他们一家生计,喂养狐狸需要马肉,父亲得经常射杀马。那天,父亲决定射杀老母马弗罗拉。弟弟在一旁摩拳擦掌,雀跃不已,姐姐却暗暗为逃命的弗罗拉敞开了门。父亲多费了些周折,弗罗拉难逃一死,弟弟向父亲“举报”,姐姐放走了马。但父亲宽恕了她,说“她只是个女孩”!门罗写女孩蹲在鸡笼前看母鸡孵蛋,眼神软得像棉花,写男孩举着枪走向谷仓的背影,坚定刚毅。是啊,男孩的爱,锋芒毕露,带着一股子闯劲,女孩的爱,宽厚仁慈,温柔得能接住风。同是爱的力量,男孩与女孩,长大后就不会是同一个模样。但敏感的人能够理解,阳刚的魄力和柔软的仁慈,照见不同却炽热的灵魂,它们,都是真的。
《明信片》里那张磨圆了角的硬纸壳,是克莱尔寄来的明信片,“我”一直觉得它占地方,可有可无。突然有一天,克莱尔娶了别的姑娘,再也等不到明信片的“我”才发现,那上面的字迹比心还烫。人有个通病——失去的时候才知珍贵,拥有时却不以为然。
《快乐影子之舞》是小说集的同名篇。日渐年迈的钢琴老师用音乐对抗清贫与孤独,两姐妹住在漏风的屋子里,钢琴键上蒙着灰,演奏也时常不完美,但教起孩子来却眼睛发亮,带着傻气的认真。充满仪式感地坚持一年一度的音乐派对,不带功利的善意里闪现着人性最珍贵的光芒。门罗没写她们多不容易,只写她们用音乐与世界对话,在孤独人生里温柔坚守;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构建温暖小世界,在困顿日子里仍然释放善意;对孩子们她们从不评判,却以沉甸甸的爱为智障小孩织就抵御世间寒凉的网。
这些故事总让我想起被人叫“老干部”的那天。一好友在群里夸另一位好友“轻盈、喜悦、智慧”,顺口说我发言像个“老干部”,她不太喜欢。都是好朋友,也明知道她在玩笑,但我心里却像被“踩低捧高”的小石子硌了下,不太舒服。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我反复地想“老干部”的形象是怎样的——正经八百?不苟言笑?顽固自大?沉闷呆板?越想越感到别扭,最后觉得是自己太过敏感了,不够海纳百川。
当我终于为反刍着的思维踩下刹车时,才厘清思绪。被人刺痛时,总先怪自己“太敏感”,我这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呢!
每当被同学起了绰号的学生红着眼眶跑来告状时,我总说:“别管他们,别人怎样看你,显现的是他们的内心世界,而你如何看自己,源于你自己!”可轮到我自己,却忍不住会“责怪自己敏感”,硬是把敏感的天性拽往阴影里。
翻着门罗的书,我更清醒地意识到,敏感是一种本事,能比别人更早摸到生活的伤口!它能让我们在被越界时清醒地说“不”,能在别人难过时给予最贴心的安慰,它会让我们比别人多尝点酸,多摸到一些暖。这哪是缺点?分明是老天给的礼物。
敏感,它是我们生命钻石中的一个棱面,它不该躲在阴影里,而要闪出光亮来。毕竟,这世上能同时尝到酸与甜、摸到冷与暖的人,才不算白来这一趟呢!就像门罗,她可能从没觉得敏感是负担,反倒让这面棱将生活小细节统统折射成了令人动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