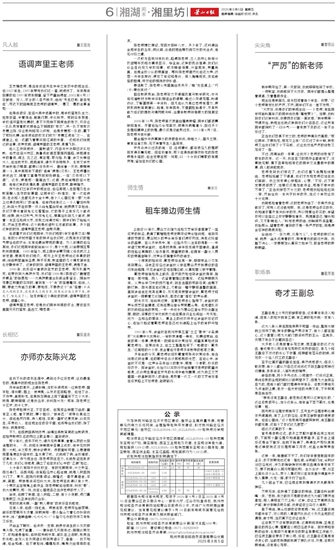■陈涌涛
在我不长的读书生涯中,遇到过多位好老师,让我最难忘的,是高中时的班主任陈老师。
开学后的某天,上课铃响,沈校长领进来一位新老师:国字脸,细长眼,唇上一抹美髭,头发浓密而略卷。他站了会,不作声,拿起粉笔,在黑板左侧由上而下重重写下三个大字,转身,眼神烔烔:这是我名字,我叫陈兴龙!那年,陈老师三十五岁,我十七岁。
陈老师脸颊方正,不怒自威。他藐视各种陋习谄佞,富有正义感,看不惯时,爆个粗口,“娘希匹!”领导也惧他三分。但他色厉内柔,待人感性,平常一副旷达豪爽样,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在任班主任的日子里,他传导给我们的,除了快乐,就是亲和。
不久,他因病回县城休养,后调任县教育局政治教研员,在培养教师队伍的岗位上敬业奉公,直到退休。
那个年代,读书不吃力,课外无所事事,看着头顶的太阳消磨时光。一天,我和永祥等同学自镇上返校,途中见村民捉一大蛇,杀之取皮,剩余欲喂狗。沛根直呼可惜,怂恿建南用草绳缚住拎回学校,盐水煮了吃。这就闯了祸,全校通报,纪律处分。作为班主任,陈老师顶住压力,也就象征性批评了几句,我们心存感激,确立了他在我们心中的“江湖”地位。
七十年代有阵子我比较空。有时无聊起来,兴之所至,四处串门。沿西河路、体育路经市心路往南,就是人民医院大门了。夏天,医院内树影婆娑,南墙边一排家属宿舍,平房,简陋。师娘是资深妇科大夫,陈老师在此得以有个家。一个男孩坐在矮凳上做作业,陈老师喊他站起来,叫我“哥”,我大受震动,那一刻,我在心里把自己当作老师的家人了。
后来,他搬了新居,在人民路,二楼,有个小走廊,进门靠左是厨卫,比正房低两级台阶。
那时我常光顾,一副“熟人要亲”的良好自我感觉。
见有人来,他俩一阵忙乱。师娘泡茶,老师开始削苹果,削好的苹果开水烫着,到厨房用一根小指头勾着毛巾拎到我手中,说:“曲嘛曲嘛(吃吧吃吧)!”小指勾毛巾的动作又夸张又好笑。
然后坐下聊天。他点燃一支烟,就像安徒生的小女孩擦亮火柴,充满了能量。——建华前几天刚来过;园园谈朋友了,你知道是谁吗;伯林和秀岐参军,部队在上海呢;张英当校长啦;金龙从北外阿语系转到英语系了,谁谁……我不知道,他全知道。他不停地说,嘻嘻地笑,嘴角泛出细细的泡沫。
陈老师博忆强记,观四方而呼八方。多少年了,还叫得出全班学生的名字,闲谈间,会适时把话题引向双方的关注点,绝无冷场之虞。
一次蛟龙自杭州来找我,路遇陈老师,三人去市心桥旁冷饮店喝牛奶和冰镇绿豆汤。毕业后,这样的机会难得,我们谈论各自近况及学校旧事。蛟龙嗓音浑厚,兴奋起来,声量渐高。他是全校公认的男高音。哪料陈老师居然比他还大声,仿若一与学生接近,便忘了年纪和身份。旁人掩嘴而笑,笑他奇怪的腔调,并对他的相貌窃窃私语。
要结账了,陈老师从兜里掏出皮夹子,“啪”放在桌上:“巧(钞)票我来付!”
担任教研员后,陈老师致力于课程改革与教学研究,参与将统编教材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题,通过公开课观摩,听课访谈,了解基层第一手资料。但凡他认为某位老师有潜力,便积极向教育局建议、疏通,东奔西走,不惜翻脸拍桌子,尽其所能为他们的提拔与调岗鼓与呼,给青年教师创造更大的施展空间。
2006年10月,陈老师首次被查出罹患肿瘤,同学们都很震惊和难受。尽管他始终乐观面对,顽强与病魔缠斗,挺过多少生理和精神上的折磨,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2013年4月7日,陈老师与世长辞。
据全程参与丧事操办的沛根告诉我,吊唁之人,里外三层,竟有汹涌之势,无不奔着先生人品而来。
岁月会冲淡过去的每一日,任何精彩,都将被经久的磨砺而变得平庸无感。但在我看来,那个在黑板前挥动粉笔的陈老师是永恒的,他注定要在那一刻起,以一个令我们尊敬的有趣灵魂,留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