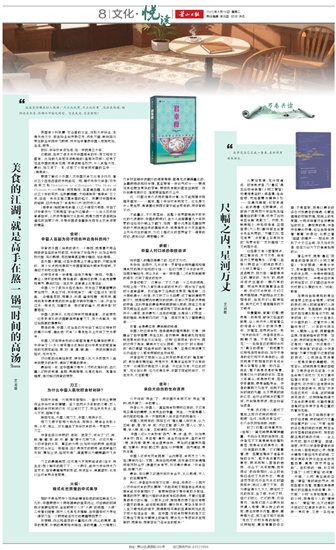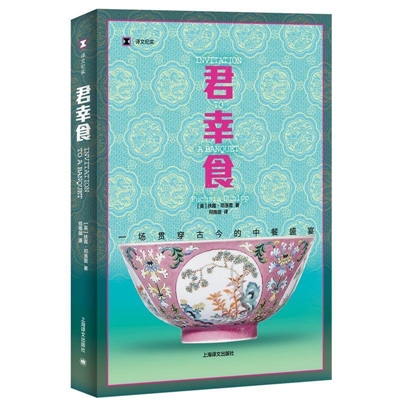文/龙烟
“这道菜仿佛在对人低语:‘只应此处有,只应此时有’,无论在伦敦、纽约还是北京,你都不可能吃到它。它在发光,它在歌唱!
英国有个叫扶霞·邓洛普的女生,剑桥大学毕业,本是天选之子,却在毕业后灵根忽开,远赴万里,跑到四川烹饪职业学院学习厨师,并开始学着像中国人那样吃饭,生活,思考。
岂料,中华饮食深如海,她一学就是三十年。
这期间,她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美食的书,英文和中文都有。比如前几年那本很畅销的《鱼翅与花椒》,记录了她在中国的美食见闻,写得很鲜活热烈,令人食指大动。最近,她又写了一本,还取了个可爱而郑重的名字——《君幸食》。
要想了解这个外国人对中国饮食文化有多内行,看这三个古色古香的字就能见一斑:据该书中文译者(该书由英文版《Invitation to a Banquet: 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转译)何雨珈说,她查遍古籍,也没找到这三个字的来历,经扶霞提醒,才知道原来“君幸食”三个字,出自一件马王堆汉墓食器的铭文。扶霞对中国美食的钻研,已然走向了“食其所以然”的历史纵深。
《君幸食》超越单纯食谱,以三十道菜为钥匙,开启了对中餐作为“文明瑰宝”的全方位解读——从灶火初燃到餐桌哲学,从历史考据到文化批判,既是为西方读者破除偏见的启蒙之作,亦是中国读者重新发现本土饮食深度的镜鉴。
食材:
中国人是因为穷才吃各种边角料的吗?
中餐被外国人诟病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喜欢用各种奇奇怪怪的食材做菜,书中举了好些例子:比如各种动物内脏、鸡爪鸭脖、尾巴脆骨甚至蝎子蝗虫,如此等等。
在外国人眼里,这些东西是上不得台面的,只配当饲料。有个论点就说是因为中国曾面临长期食物短缺,不得已才去吃这些东西。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唯一原因。中国人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哪怕拿到一副稀烂的牌,也能凭智慧和勇气,最后打出一组王炸,在餐桌上也是如此。
中国人为了做好这些边角料,开发出了更高智慧的烹饪技巧。其他不说,书中就举了一道“红船划水”的菜品,一条鲤鱼尾巴,用高汤、料酒、酱油和糖一起来炖,直炖到其中最滑嫩的胶质全都与锅中物融为一体,产生如红木一般深沉、如重奶油一般浓郁的酱汁,吃得作者“欣喜若狂”……
中国人的筷子,也和这种食材相得益彰。你能想象一位彬彬有礼的法国酿酒师拿着刀叉,努力去解决一块红烧鹅掌的情景吗?
更绝的是,中国人还给自己开发出了适应这种食材的高级口感,借此把“饮食”从填饱肚子上升到了艺术享受。
中国人对每种食物的口感都有着严格精细的要求。书中举了50多个词来描绘边角料在口中激发的感官愉悦的无限可能性:嫩、软、滑、潺、脆、酥……像武林高手的招式,无穷无尽。
对口感的创造性探索,使中国人比大多数西方人品尝到更多的食材,得到了更高的享受。
最后说一句,在中国真不是穷人才吃边角料的,古代富人们吃的熊掌、鱼翅、燕窝等等,也是边角料。其奢华程度,绝对超过西餐的想象。
刀工: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把食材剁碎?
和西方动辄一大块烤牛排相比,一盘炒牛肉丝要更符合中华饮食的精髓。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放入羹中的食材就被切片、切丝或切丁了,历经岁月变迁,至今不变、回响不绝。
原因无他,外国人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尔。
用刀叉便于取用大块肉类;而筷子,更适合夹取小块、小片、细丝。这也催生了中华饮食的另一项绝技——刀工。
作者在四川学厨时,领到一把菜刀,学会了“切、剁、刨、锯、砸、抹、刮、片、敲、捶”等十几种刀法。这还只是一个初学者的水平。真正的大师,比如扬州的厨师,能把豆腐切成头发丝一般粗细;古代贵族家的厨师,能把鲈鱼切片到“薄如丝缕,轻可吹起”,简直要化为蝴蝶翩然飞去……
刀工的最高典范,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庄子.养生主》那个解牛的庖丁了。一个厨子,能作为中华技术乃至艺术、哲学最高境界的象征,传颂至今,虽属虚构,也足以让饮食界与有荣焉。
火候:
程式化世界里的中式美学
相较于麦当劳炸个鸡块能精准地把时间控制在几分几秒,中国要想炒个同样简单的韭菜肉丝,对出锅的时间就没有硬性规定,全在厨师个人对“火候”的把握。“火候”二字看似随意,西方人尤其无法理解,在中国却成为考验一道菜乃至一个厨师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你想啊,肉丝和韭菜的分量和比例、肉丝的厚度、韭菜的嫩度、炒锅的厚度和传导性、油的用量、火力强度以及食材在锅中被翻炒的速度等等,都是无法精确量化的,全靠厨师的现场发挥,甚至带有一定运气成分——更何况其他更加复杂的菜肴,要把所有配料都在出锅那一刻炒到最完美状态,难度更呈指数级上升。
这一切都没有办法用数据来计算,也不能用操作规程来框定——一框定,整个中华饮食就完了。这也是为什么麦当劳、肯德基这种西式餐饮能全球连锁,而中餐就不行。
不能量化,不代表落后。在整个世界都趋向于数字化的大浪潮中,中国的厨师们,在大火后面靠着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将炒锅上下翻飞,如同一辈子沉浸在笔墨世界中的大师创造出来的高超书法,或是抽象派大家在画布上天马行空的画作,为这个程式化的世界留下一道美的印记,满足口欲,更慰藉心灵。
新鲜:
中国人对口感的极致追求
说中国人的嘴巴是最刁的,应该不为过。
书中说,在西方,几乎没有一家餐馆会特别重视和强调食材的原产地和时令性——他们习惯了冷冻的食材,如同牛嚼牡丹,何必多此一举?而中国人,对食物新鲜度的追求,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作者记载了一次宴会:“不久之前一个三月的傍晚,我和上海一家私人餐饮俱乐部的成员们一同参加了当地时令佳肴盛宴。我们品尝了经典的本帮菜‘腌笃鲜’,汤汁美味得令人叫绝;我又吃了淡水田螺,还了解到清明节前不久,就是田螺肉质最好的时候;还有以苏菜做法烹制的甲鱼:主料甲鱼的最佳赏味期限稍纵即逝,而在三月油菜花期恰正当时,所以这道菜用了菜籽油来做。全宴一共十八道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也是将人们聚在一起的理由,就是银闪闪的‘刀鱼’,每年只有几个星期最应季……”
你看,全是最应季、最新鲜的味道。
中国人吃应季食物,绝非简单的营养摄取,它是一种融合了哲学智慧、养生实践、自然崇拜、情感寄托和纯粹味觉享受的综合文化体验。这种“应季而食”的行为,同时滋养了身体、精神与文化认同感。那份对“时令美味”的“迫切渴望”和品尝后的“愉悦心情”,正是这种深厚文化内涵在个人感受层面的生动体现。
作者在吃了用刚从山上挖来的笋做成的“腌笃鲜”时,激动得手舞足蹈、灵魂升天,激情洋溢地写下这样的文字:“这道菜仿佛在对人低语:‘只应此处有,只应此时有’,无论在伦敦、纽约还是北京,你都不可能吃到它。它在发光,它在歌唱!”
食补:
来自大自然的生命滋养
终于说到“养生”了。讲中国饮食而不与“养生”挂钩,就失掉了一半的意义。
作者认为,中国人一直坚持食物要吃应季的,不仅有现实情况的需要,也有养生的考量。养生,一方面是靠人体内部的和谐,另一方面就是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中国人把特有的“阴阳五行”理论融入到饮食,认为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五脏: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五味调和,滋养五脏。
中国人还认为食物有“四气”:寒、凉、温、热。比如寒凉食材(西瓜、绿豆等)清热,适合热性体质;温热食材(姜、羊肉等)散寒,适合虚寒体质。烹饪时注重寒热搭配,如薏米(凉性)配红枣(温性)以护脾胃。四气调性,寒热平衡。
中国人还讲究药食同源:“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引自《黄帝内经》,下同),身体出现问题,优先通过饮食调理而非药物治疗;提倡饮食有节,反对暴饮暴食:“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最后,将口腹之欲提升到饮食合欢、礼仪载道、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所以,作者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一个西方人对中华饮食的顶礼膜拜:“我越来越不相信有任何其他美食能与中餐相比了。首要原因倒不是中餐的多样性、精湛的技艺、冒险大胆的创新或纯粹的美味,尽管这些都是很有力的论据。从根本上说,原因是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的美食,能将敏锐洞察、精妙技术、复杂多样与对人生之趣纯粹的追求,同健康和平衡的自律原则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好的食物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当下身体与精神上的愉悦,更会充分考虑到你在用餐时、用餐后、用餐翌日乃至余生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