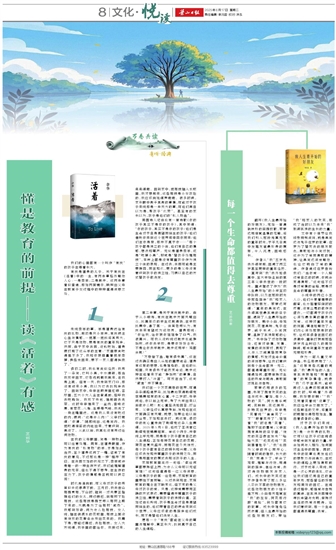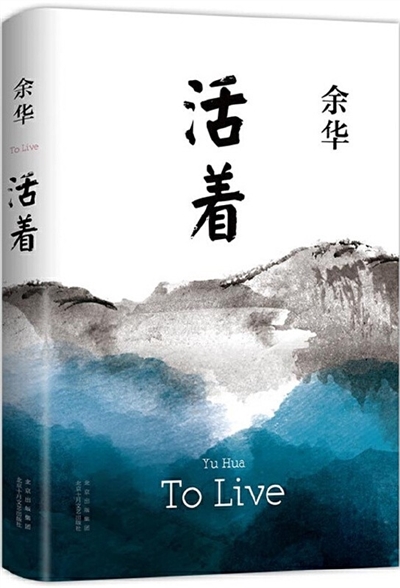文/刘华
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叫作 “有庆” 的孩子在等着长大。
有庆是福贵的儿子。关于有庆在《活着》中的一生,有两件事格外触动人心:一是卖羊;二是跑步。这两件事看似普通,却如两面镜子,映照出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的种种值得深思之处。
先说卖羊的事。羊是福贵送给有庆的礼物,起初是只小羊羔,有庆倾注心血与情感,一把草一把料将其养大,它不只是动物,更是有庆的童年玩伴。然而,由于家中贫困,没钱吃饭,福贵便打起了这头羊的主意:“家里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我和你娘商量着把羊卖掉,换些米回来,要不一家人都得挨饿了。”
读初二时,我也有类似经历:我养了一条狗,它叫小黑,十分健硕,每当我放学回家,它老远就朝我跑来,往我身上跳。但有一天,我走到家门口,却没有迎来小黑,我以为它去找玩伴去了。回到家中,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客厅里,五六个大人坐在餐桌前,招呼我去吃晚饭。我放下书包,端起碗去夹菜。这时母亲端来了一盆肉,香味浓厚,有葱花、八角、生姜等气味,我夹了一块往嘴里送。这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肉,便问:“这是什么肉?” 父亲打趣道:“你猜。” 随即说出,这是狗肉。我把咬得细碎的肉吐出来,才意识到,小黑没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养过任何动物。
在我的父母眼里,狗是一种物品,可以任意处理。同样,在福贵眼里,作为有庆的 “私有物”的羊,亦是如此。当然,至少福贵还问了一嘴,征询了有庆的意见,不过那也是一种“程序”而已。在贫困交加的状况之下,卖羊或许是唯一的一种生存方式,我们能理解福贵的无奈,但也不得不思考,在生存的压力下,孩子的情感是否就可以被忽视?
时代奔涌向前,可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似乎还停滞不前。三月初,我去吉山梅园赏梅,下山时,碰到一对夫妻正指挥他们的女儿,爬过栅栏,到梅树下捡梅枝。这些梅枝是园艺师从梅树上剪下来的,大概是为了给梅树“减负”。我感到好奇,问为什么捡梅枝。女人说,插在装满水的花瓶里,梅枝上面没有绽放的花骨朵会开出花来的。我蹲下身,想钻过围栏,去捡梅枝。女人大方说道,我手里的都给你。我接过来,连连道谢。回到家中,把梅枝插入水瓶里,我才想起来,这些梅枝是小女孩捡的,我应该向她道声谢谢。很多时候,家长眼中微乎其微的事情,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却是一件天大的事,可他们常自以为是,帮孩子“代劳”。甚至有的家长以为,孩子是他们的“私人物品”。
美国诗人纪伯伦有一首诗歌《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其中写道:“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情感、想法和尊严。无论是福贵卖羊,还是“吃掉小黑”,抑或是“替孩子处理梅枝”,本质上都是没有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表现。在过去,贫困可能是主要原因,而在现代,更多的是父母没有意识到孩子的独立性,习惯以自己的方式替孩子做决定。
第二件事,是关于有庆跑步的。由于从小锻炼,有庆在跑步方面天赋出众,比高年级的学生还跑得快,在学校比赛中,拿了第一。体育老师认为,有庆未来有望成为运动员。福贵却说:“你给我、给你娘你姐姐争了口气,我很高兴。可我从没听说过跑步也能挣饭吃,送你去学校,是要你好好念书,不是让你去学跑步,跑步还用学?鸡都会跑!”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在过去确实是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福贵有这样的思想,也是难免的。在他的认知里,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跑步这种在他看来不能 “挣饭吃”的事情,自然要打入“冷宫”。可放在当下,这句 “箴言” 并不精准。
我们在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可谓条条道路通罗马,比如最近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赵心童,十二岁时,母亲问他,你以后上完学,考了大学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赵心童坚决地回答,打台球。父亲经过认真思考后,发现他在这方面确实有天赋,就想,如果让他以后打台球,不如现在去打。就这样,读初中的赵心童走向了斯诺克这条人生赛道。2025年5月6日,他成了亚洲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举这个例子,并非说上学无用,而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如每种花有自己的花期,荷花在夏天盛开,而梅花在冬天绽放,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父母应该去发现并尊重孩子的独特之处,而不是用固定的模式去规划孩子的人生。
家庭教育里流行一句话:“做任何事都要持证上岗,为什么父母可以无证育娃?” 这句话值得每一位父母深思。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过去到现在,家庭教育的理念在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只是,这种爱需要用正确的方式表达,需要懂得并尊重孩子的独立性,需要看到孩子的独特价值。正如纪伯伦所说,孩子是生命对自身渴望而诞生的,他们带着自己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父母应该做的是陪伴他们成长,而不是替他们决定人生。
愿每一个 “有庆”都能在父母的尊重与理解中,真正长大,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